林枫 孙杰 | 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
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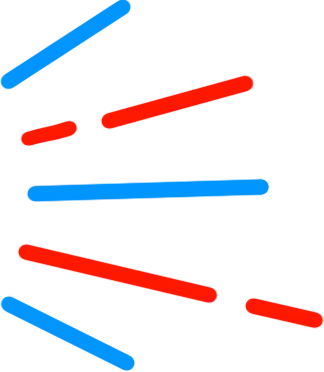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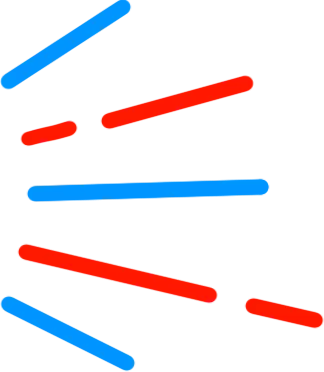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财政金融史、闽台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孙杰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义冢不仅体现了清代台湾的传统中国色彩,且可以作为今人探讨台湾社会特质的凭借。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侵垦与盗墓、勒索等方面。针对义冢的破坏,官方制定相关法规、坚持“息讼“原则、采用示禁的方法,民间则自行发展出一套约定俗成的处罚措施。然而,围绕义冢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台湾所独有,这体现出清代台湾与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较多的相似性。这些社会问题既反映出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色彩,也印证了其作为移民社会的移植性特征。
关键词:清代台湾 义冢 边疆社会 移民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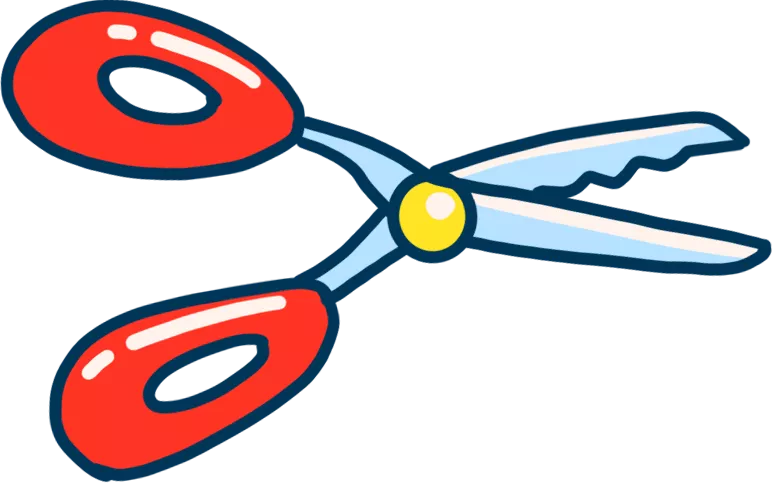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之后,清政府限制移民台湾的政策时有变动。但对闽粤人民而言,这种时松时紧的限制政策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义。大陆移民不顾政府禁令,通过各种途径冒险渡台。他们为台湾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并在许多方面给台湾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义冢即其一。
根据《台湾省通志》,有清一代,台湾共设立义冢170余处,分布范围遍及台湾、凤山、恒春、嘉义、云林、彰化、新竹、苗栗、淡水诸县及基隆厅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义冢不仅体现了清代台湾社会的传统中国色彩,而且可以作为今人探讨清代台湾社会特质的凭借。本文主要利用清代台湾地方志书及《淡新档案》,以义冢的破坏、维护及相关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借以窥视清代台湾社会的某些面貌。
清代台湾的义冢多以地方士绅、郊商等担任董事、经理诸职,负责其日常维护,但如《凤山县采访册》所载该县昭忠祠及义冢那般严密细致的管理章程,毕竟是少数。尤其是清前期的台湾,一般的义冢多“无人看守,向惟官斯土者同尔绅衿留心稽察,共相保护”,有些义冢“历年虽有山差,亦奉行故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义冢屡遭破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
实施丧葬救济,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逝者归葬土地。义冢既为丧葬救济最重要的设施,土地便成为丧葬救济最重要的载体。冯贤亮对江南义冢的研究表明:明清江南地区一度盛行火葬,而同治以后,经咸丰太平天国之乱,大量无主荒山、荒地的出现,为官方提倡土葬、建设义冢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为消弭火化之风创造了条件。可见,义冢的设立常常以存有足够利用的土地为前提。而另一方面,义冢的破坏也多表现为土地载体的被毁。
总体而言,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以遭受侵垦最为突出。此外,又有盗墓挖坟、勒索丧家、借尸图赖等社会问题。
(一)侵垦义冢
义冢之所以屡遭侵垦,与大量无主荒地及相对模糊的土地所有权有很大的关系。在清代台湾,众多未开发的土地,不明晰的土地所有权,常使得土地纷争不断。义冢土地的所有权尤为模糊,更容易遭受侵占。
1.大量未垦荒地的存在与土地所有权的模糊
台厦道高拱乾《劝埋枯骨示》云:
照得见骨则瘗,遂号仁人;舍地而埋,爰称义冢。诚以恻怛之心,亘古今而如一者也。台湾地经初辟,田尽荒芜,一纸执照,便可耕耘;既非祖父之遗,复无交易之价。开垦止于一方,而霸占遂及乎四至,动连阡陌,希遂方圆。已完课额者,虽曰“急公”;尚属抛荒者,难免垄断。致穷民欲博一坏[抔]之土,而豪强视为世守之业;非管事之勒资,则佃丁之索价。同为官地,均可蒙庥,尔既可以营生,彼独不可以送死?揆之情理,岂得其平!除行府、县知照外,合就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台属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凡有未垦荒埔,果系官地,听民营葬;若系批照在民,未经开辟者,亦准附近人民营葬,不许阻挠!如有管事、佃丁借端勒索,许赴该县控告,以凭究治;亦不许将人家已辟之地,借称营葬,希图侵占。敢有故违,一经告发,各治以罪。慎之,毋忽!
谕示可见,清代台湾,一方面存在着大量无主未垦荒地,另一方面,又因为“开垦止于一方,而霸占遂及乎四至”而形成更多的有主未垦荒地,许多垦户从官府领取垦照,却将领垦土地大片抛荒,以达到垄断目的。因此,高拱乾在晓谕中强调,无论已经批照与否,未经开垦的土地都应“听民营葬”。
谕示还反映了清代台湾土地所有权的模糊。高拱乾在强调未垦荒地“听民安葬”的同时,严禁借营葬之名侵占他人“已辟之地”。既是“已辟之地”,本该产权明晰,在台湾却可能遭遇侵占,可见土地所有权在台湾社会中尚且呈现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清代地方官员也屡屡提及台湾土地所有权的模糊及其负面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与清政府对台湾的认识、对台湾的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直至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之前,台湾始终被视为王朝的海疆、东南四省的屏障,军事战略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清廷过分忽视对台经济层面的经营,特别是在光绪年间刘铭传全面清赋之前,台湾土地丈量不清、赋额混乱的问题尤为严重,极不利于土地所有权的明晰。清代台湾“汉番杂处”,移民偷越“番界”私垦土地的行为从未停止过,而番汉之间买卖土地的做法也长期存在,这就加剧了土地关系的复杂性。移民开垦过程中形成“一田多主”的局面,土地产权不明,有碍于土地买卖,易于发生产权与田租的纠纷。
2.侵垦义冢现象
清初,台湾各地荒山荒埔,听民安葬。但随着移民拓垦的加快,可垦耕土地越趋萎缩,侵垦义冢的现象遂相应增多。乾隆以降,台湾各地得以迅速开发。嘉庆以后,侵垦义冢的情形便愈发多见,这由大量示禁碑的出现可以得到印证。据曾国栋《清代台湾示禁碑之研究》一文的统计,文献所存冢地类示禁碑32件,其中嘉庆及其以后出现的多达27件。
以噶玛兰地方为例。道光九年(1829),总理杨德昭等禀请于山场设义冢,噶玛兰通判洪煌出示晓谕,严禁侵垦。然而,示禁木牌于数年间即已腐朽。道光二十九年(1849),街庄各头人黄缵绪等即报称牌示已毁,通判杨承泽遂再次出示晓谕,并重新泐石。至同治十一年(1872),进士杨士芳等又佥称,“但前谕未行,迄今年久而弊混又生。兹据该处庄民报称,近来有人在义冢界内植木种茶,芳等往勘属实。若不仰恳宪恩重示立碑定界,窃恐奸徒效尤,争利占地,将冢愈混而愈灭,不几令死者无葬身之地乎!芳等目击心伤,爰敢沥情禀乞恩如所请,准即再示立碑定界,以杜混占。”为此,通判洪熙俦只得又一次出示晓谕:“四围山等处留为冢地,从民埋葬,前经出示勒牌定界有案,岂容弊混侵占。自示之后,凡属义冢界内,不许山鬼虚响坟堆、借词勒索,亦不许附近居民种茶、植木,侵占寸地。倘敢故违,一经绅董指禀,定即严拿究办。”民间自发的侵垦行为,从未停止过,针对侵垦的示谕也只能“喋喋不休”地反复重申。
前文提到,一旦涉及土著居民,土地关系愈加复杂。由于许多“无主荒地”被土著居民视为狩牧之所等原因,人们很难在“无主荒地”和“番地”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一些垦户遂利此漏洞,“串通社番”,强占公冢。《淡新档案》中不乏此类案件,例如:
具佥呈。监生林绍贤、廪生郭成金、林长青、郑用锡、生员郭菁英、郑用钦、郑光华、林栖凤、监生朱朝阳、罗秀丽、温玉树、铺户振利号、益三号、茂兴号、金和号、德春号、建兴号、耆老陈大彬、周朝赛、吴仕提、许仕沛、王仕凤、张福载、温元三、王仕柔等为葬身无地,人鬼含冤,佥呈鉴察,乞准示禁事。窃惟人死以土为安,生斯葬斯,理之然也。缘堑城之东南,自金山面大崎双溪口起,直透至盐水港老衢崎止,悉系高山峻岭、层峦叠嶂,原非有主物业,听民间择穴葬坟,久成坟山冢地矣。近有图垦界外埔地之人,串通社番,以设隘为名,于嘉庆十九、二十等年纷纷佥呈,瞒蒙薛分宪批准,未经请勘定界,即自建隘,占管埔地,混将久葬坟茔犁掘毁坏,仁人见之,莫不心伤,以理晓劝,便说奉宪开垦,孰敢出阻等语。坟主巡觉,欲行修理,多被需索,直以界外之荒山,占为奇价而取利也,若不请示严禁,将见堑民生有托足之区,死无葬身之地,人鬼含冤,惨伤曷极?兹贤等秉公佥议,应将金山面大崎双溪口起,直至盐水港老衢崎止一带高山峻岭,及崎零高阜处所,仍为坟山冢地,听民择穴葬坟,毋许借隘占垦伤碍,如敢混行掘毁,一被坟主指控,即严加究治;其余坑涧有水可灌,又无妨碍已藏坟茔之荒埔,堪以开垦田园者,即听建隘之人开垦为业,亦已不少矣。如此设法立定章程,既有隘地,又有坟山,是养生丧死无憾,而彰王道以感宪恩于生生世世矣。是否妥协,合无佥呈,伏乞大老爷西伯仁政俯如所请,恩准出示晓谕,俾便勒石永远遵行,幽明沾感。切呈。
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具佥呈。
据此可知,竹堑城东南山地,本属无主荒山,当地居民长期以为冢坟埔地。但有些垦户串通土著居民,借口设隘,向官方报垦。官方往往不明就里,直接批准报垦请求。在实际开垦过程中,垦户又多不顾坟冢,任意侵占,甚至勒索坟主。
本来,拓垦当以可耕平地为目标,坟冢多在高阜之处,两不相涉,同治年间“柳波状告温阿佛将柳波故兄所骸毁灭、占地筑陂”一案中,职员刘逢时等即认为,“陂宜低湿,方得聚水难枯,而坟宜择高干,可保□□□……陂互异”,故此案为柳波影射冒控,希图索诈。可是,侵垦坟冢引起的民事纠纷却确实大量存在,固然有“有水源、肥沃、易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大片的荒山荒埔往往就成为开垦的目标”方面的原因,而土地所有权模糊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诱因。
3.侵垦义冢的社会影响
侵垦义冢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引发纠纷、破坏生态等方面。
在清代台湾,侵垦冢地引发了许多民事案件。因为侵垦冢地既涉及经济利益,又关乎道德习俗。例如,在冢地掘取沙土、开采山石,常被视为“致碍县治龙脉”的做法,为民间所忌讳。
侵垦冢地,不仅可能导致民事纠纷,有时甚至还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乾隆年间,竹堑垦户曾合捐银一千圆,向竹堑社通事丁老吻承下凤山崎埔地,作为附近居民的牧场、冢山。到光绪时,民人刘春连等串通“社番”钱文健假造垦批,掘毁冢地,阻挡牧牛,意欲侵占该处牛埔冢地,由此激起当地民众的公愤。当地居民纠众掘毁了刘春连所种茶丛,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侵垦又对自然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造成生态的破坏。侵垦者锄铲草皮、滥伐冢地树木,甚至掘挖沙土山石,破坏冢地植被,“又有不法之徒,掘取红涂,挖卖山石,毋论县龙过脉、人家坟茔,尽行挖坏”。嘉庆年间,拔贡生李宗寅等就曾严厉指责破坏义冢的滥挖滥砍行为:
台郡南、北义冢,概系沙土浮松,全赖蔓草滋生、根连固结,以资护卫。近有樵夫牧子,在该坟冢锄割草薪、放牲践毁、刨取沙土,妄肆蹂躏,渐致坟土摧残;一经霪雨,水注沙流,恒有冢穿棺现之虞,已堪悯恻!
又如《三块厝义冢示禁碑》亦云:
保内三块厝牛埔头、东山黄厝庄、犁头厝埤仔头、锣钹蒂、赤涂崎等处荒山,自古设立义冢,以为附近民人埋葬之地。屡因不法之徒,奸贪渔利,盗挖赤涂、砂土、树头,以致山崩石坠,骨骸暴露,不可胜数。
侵垦行为,破坏了义冢及其周边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恶果,甚至露棺暴骼,惨不忍睹。对此,民间常常立碑约定,对冢地环境加以保护,对滥采滥挖者加以处罚。
(二)盗墓挖坟与勒索丧家
据文献记载,清代台湾有所谓“山鬼”者,专门从事盗坟挖墓、敲诈勒索的勾当。台南市南区墓地原立有嘉庆七年(1802)台湾县《义冢护卫示禁碑记》,称台郡南、北义冢,“更有一种奸徒,绰号‘山鬼’,胆将牌石、坟砖偷挖盗卖,甚至开棺盗物,或迁骸别瘗,将穴筑窨转售,种种惨伤,殊难言喻!”
又,嘉庆二十年(1815)彰化县《官山义冢示禁碑》载:
甚有一种奸民盘踞坑仔内,绰号“山鬼”,私筑窨堆,以索银元。从则得葬,忤则行凶。往往棺柩抬至山上,富者任其糟索,贫者莫可如何。又有不法之徒,掘取红涂,挖卖山石,毋论县龙过脉、人家坟茔,尽行挖坏。
后一则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官山义冢安葬的对象不仅止于“穷民无力安葬并无亲族收瘗”者,还有一般平民,“山鬼”已经将丧事作为一种勒索的借由,有钱的丧家更成其勒索的对象。
勒索丧家最为典型的当属“恶丐”一类。清代台湾,流丐党索,肆横无忌。现存高雄县紫竹寺内的道光《奉呈主示禁》碑记载:举凡村民庆寿、酬神、演戏以及嫁娶、追荐功果、庙宇演戏者等事,流丐自称“大例”,拥聚强乞,要钱要饭。从则无事,不从则聚党闹事。
因为流丐、恶丐遇民间婚丧各事多行强乞,台湾地方出示多项禁约。乾隆三十九年(1774),凤山县知县刘亨基应庄民所请而颁《奉禁恶丐逆扰碑示》,该碑示云:四季凡有田业各户,每季给钱二十一文(无田穷民不许索);嫁娶原例,丐礼番银二钱;抱养成婚,止有男家丐礼二钱,不得另索,女家亦不得倍取男家;演戏赛愿,例同吉礼,番银二钱;士人进身,例同婚吉,丐礼二钱;丧忏功果,正人子研痛惨切之时,原非美事,例无丐礼;赛乐安宅,以及作清蘸,此系祷尔上下,非因婚吉,无丐礼;丐首即收四季,并诸吉礼,例应收养流丐,不得仍纵散乞滋扰。
道光中,台湾县知县胡国荣重申前令“仁德北里旧规”,凡遇民间婚嫁、酬神及追荐功果、一切丧喜各事,丐首可以要求民间给钱,但不可纠众强索,其中,庄民丧事功果,应给丐首钱六十文。光绪五年(1789),凤山知县邓嘉绳应士绅的吁请,仿照“前县示禁规条”,再度开列示禁,规范乞丐乞讨行为,只要不多取强取,乞丐可以借许多由头向民家要钱,“遇民间丧事,有力之家,无论斋忏几天、竖立几幡,皆给钱二百文;如无斋忏、竖幡之事,量力酌给。”
将上述乾隆、道光、光绪三块碑示加以比较,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官方对乞丐行为的规定渐趋细化,规范渐趋成熟,对乞丐勒索的钱额也有所调整,在允许乞丐勒索的范围上呈现出更为宽松的态势,即如对于“丧事(丧忏)功果”,乾隆碑尚认为“原非美事”,不应借机勒索;道光碑则明白规定,亦应给钱六十文;光绪碑则指出,应当区分是否为“有力之家”。对于流丐的勒索行为,官方并未绝对禁止,而是采取了折中式的处理办法,“灵活性策略”的背后,意味着乞丐勒索丧家等行为的普遍存在。
台湾土著勒索丧家的现象,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台湾官府对于土著居民的管理不甚完善。相传平埔族内有所谓“棍番”者,逢人埋葬,即借口索要“花红”。非但如此,他们还常于粮食收割后,挨户索粮。另一方面,一旦牵涉到土著居民,土地所有权归属就很难明晰。有些土著居民利用这一漏洞,行勒索敲诈之事。光绪年间,彰化县大肚堡士人曾禀称:
本堡八张犁庄与该处迁善社比连,番民杂处。每有棍番相传套语,借以民间置买田园,无论何地,概属番垦,是以勒索习以常,名曰社规。凡遇庄民丧喜等事,迭自呼男唤女,聚党呵声,到处借索。富者任其取携,免受糟蹋;贫者告以困乏,每被横行。
因此,借口勒索、阻挠丧葬之事,亦有土著居民的参与。
(三)借尸图赖
丧葬救济的重要对象是无人或无力收葬者,义冢为重要手段,一方面是人们积极创造条件,使死者入土为安;另一方面,在清代台湾移民环境中,有些死者非但不能得到救济,甚且可能成为勒索图赖的借端。借尸图赖者既有各式游民、棍徒无赖,也有“玩保、蠹差”。
前文被称为“山鬼”的人,多半属于游民群体,在清代台湾,无业游民更被习称为“罗汉脚”。以“无田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贾、不负戴道路”为特征的罗汉脚,游手好闲,“遨游街衢,以讹索为事”。在社会动乱时期,他们参与各种动乱;在常态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也多行不法,冲击社会秩序。他们生无所依、死无所葬,本属于丧葬救济的对象,却又常常盗坟挖墓、勒索丧家,因此成为官府颁发示禁、禁止讹索的嫌疑者。除了嫖赌、摸窃、械斗、树旗等恶行之外,借尸图赖也是他们的“牟利途径”。
乾隆年间,台南商民李文兴等曾禀称:
兴等客寓台郡,经营生理,感沐鸿仁,共庆春台。只因城隍市镇,人民杂处,多有游手好闲,不事生业,赌荡之徒,日作流丐,夜宿庙观,流落疲病,卒于路旁。市民共施棺木,地保为其收埋,往往有之。近有无赖棍徒,混号罗汉脚,竟将疲病流丐,黄昏暮夜,抬背吓驱,稍不从欲,丢镇门首。一经嚷闹,多提号灯,借称打听差查,纷拥琐索,延搁而死,街邻多受差扰。
后来,该县生员凌崇岱等再次呈称:
切岱等各庄,欣逢盛世,安居乐业,毫非不染。冤有不事生业,赌□□徒,绰号“罗汉脚”。结党成群,日为流丐,夜行鼠窃,身穷计生,靡所不为。暮夜之间,且将病毙丐尸□□殷实之家,或丢田头、园尾、街衢、路巷,或移吊园头、树木,借尸吓骗,以致差保到地查视,不肯收埋,□索分肥,为害不浅!
人命大事,于官于民,均怕沾染,“罗汉脚”就利用人们这种畏惧之心,制造恐怖气氛,事先放出风声,随意罗织,吓诈平民,借调处以得利。游民借尸图赖,在清代台湾绝非偶然现象,光绪元年(1875)、光绪二年(1876),崇德里、长兴里、新丰里等处,屡屡出现倒毙路边、实无亲属指认的尸体,被无赖棍徒“借尸吓诈”,福建巡抚王凯泰、台湾府知府周懋琦、署台湾知府孙寿铭等为此相继示禁。
借尸讹诈者,还有具官方、半官方身份的地保、差役等。例如,诸罗县,“台地五方杂处,多游手,不务生业匪丐流落,一遇病毙,地保串棍,乘夜台背诈索;如不从其欲,则丢锁门首,勾通县差,带同白役,借命除害。”盐水港街,“无赖匪徒,串谋奸保蠹差,将病毙丐尸,或路通倒毙不识姓名身尸,移置田园屋角,牵连地主邻佑多人,任意婪索,大为穷檐蔀屋之累!”不务生业的乞丐流匪棍徒等死于路旁僻处,地保、差役等视为利薮,报官之前,先行索诈发现尸体附近的平民,恐吓捉拿。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一种情景,即直接谋害外来乞丐,再勾结无赖棍徒,由其冒充乞丐亲属,以尸亲身份图赖。
二
为使义冢免遭破坏,清代台湾官方与民间均作出了努力。这些努力,包括惩罚性质的消极性措施与预防性质的积极性措施。
(一)官方的“息讼”原则
坟冢不仅仅是死者安祥之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诸多信息的一个文化符号,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对于为害丧葬的相关行为,《大清律例》处罚严厉,仅发掘坟墓就要受到徒、杖之刑,开棺见尸则要处以绞刑:
凡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监候)。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为从,减一等)。若(年远)冢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尸在柩未殡,或在殡未埋)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杂犯)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准凡盗论,免刺。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御史良弼奏,“发冢案件,层见迭出,请多严定章程”。新章程经军机处大臣讨论修改,得到光绪帝的批准。光绪十三年(1887),该新章程移知台湾知府雷其达,并由雷氏转饬台湾各地方官。
严格的律例固然是清代台湾地方处理义冢破坏事件的基本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所辖政区内是否“争讼省息”,也是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是否能够“以德化民”、推行教化的表现。因此,地方官吏在管理地方社会时,往往秉持“息讼”原则,竭力减少争讼,清代台湾义冢相关纠纷的处理也不例外。
前述垦户侵垦竹堑城东南山地义冢一案中,官方即在“息讼”、消弭纷争的原则之下作出批示:
设隘防堵生番,原系地方要务,垦埔作为口粮,亦属以公济公。薛前厅因金山面一带地方,时有凶番出没,谕饬建隘募丁,以资捍卫。旋据垦户郭陈苏占得土地公坑东起至金山面一带,郑应春占得土地公西起至枋仔林,准将埔地各自开垦,并给示晓谕在案。查该处一带均系官山,并非有主物业,该垦户等岂可将他人久葬坟茔,以借设隘开埔混行犁毁,一经指控得实,定即从严究办,断不稍存姑息。但该处附近民人,亦不得将建隘开垦成熟田园混行埋葬,以致彼此争控,今本分府酌为变通,该生等即同郭陈苏、郑应春于土地公坑东、西两处界内公同会议,如系高阜处所不能垦耕之地,即听民人安葬,庶几幽明均各相安,可即公同呈复,以便给示勒石遵行可也。
首先,官府承认设隘垦埔的必要性,而垦户郭陈苏、郑应春的占垦行为,亦为官府所允许。与此同时,官府又明令禁止借口设隘开埔来损毁冢坟的行为。其次,对于附近居民“将建隘开垦成熟田园混行埋葬”的做法,官方同样明令禁止,以杜绝纷争的发生。最后又声明,高阜不便垦耕之地,听人民安葬。
也有官府直接将民人争控土地判作义冢的情形,彰化官山义冢即为一例:
彰邑自建县以来,东有快官山,西有八卦亭山,南有赤涂崎山,北有辘沙坑山。前因杨、林二家互相争控,以致前主苏勘定一尽判作官山义冢,任民生樵死葬。
又如,道光七年(1827),淡水同知李慎彝以郭、陈、苏三姓控争埔园缠讼不休,谕饬城工总董曾青华等筹款置买并据郭棠棣自行禀充,设土地公阬埔顶义冢。在上述事例中,地方官员将存在争议的土地判作义冢,有效中止了纷争的继续。
(二)官民联手示禁
坚持预防胜于治疗的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经营策略。对地方官而言,对犯禁者实施法律制裁,并不荣耀,因为它会被视为“教化不行”。因此,杰出的社会管理者总是寻求防患于未然的办法。“示禁”,即以告示民众的方式禁止某些不合礼法的行为,是诸多预防性办法中的一种。与此同时,民间在遇到有悖于道德习俗乃至于触犯官方律例的行为时,除“送官究治”之外,禀告官府,申请立碑定界,加以示禁,也是一个重要选择。清代台湾地方就义冢相关问题也有不少示禁文书。
这类示禁碑,大多以禁止侵垦义冢土地为主要内容。即便是在竹堑附近地区拓垦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号称全台最大隘的“金广福”团体,也不能随意占垦义冢土地,咸丰《宪禁冢碑》即云:
尔等当知掩骼埋胔,古有明训,岂容借端阻葬,任意践踏!自后如系山场埔地,经各前宪先后捐买义冢牧场界内,概听民人随处瘗葬。该处居民不得再行混占冢界,私垦耕种。即金广福垦界内旱瘠埔窝、无碍田地坡圳者,亦应听人瘗葬。惟垦费所需、隘粮攸关,准予酌给番银帮贴垦户,或三元,或五元,随力措办。倘若修筑,毋许阻索。即在平时,亦戒戕伤。庶几生养有地、死葬有方,以安幽魂。该民人等亦不得在别人契买界内,藉端占筑虚堆,希图售卖渔利,致干查究。
与此同时,假借修造义冢以阻碍垦种的做法,也在示禁之列。
对于盗墓与勒索行为,官府也多采用类似的做法。嘉庆年间,台湾知县周作洵出示禁谕:
其挖坟窃物、迁骸盗穴,益干斩遣重罪,在尔匪徒诚牟利无多,何身命不惜!至义冢应听择葬,亦毋许借窨勒索!
至于流丐借丧党索、借尸图赖,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等更有不少相关禁约,如《奉禁恶丐逆扰碑示》(乾隆三十九年)《县主示禁碑记》(乾隆四十七年)《严禁开赌强乞剪绺示告碑记》(乾隆四十七年)《严禁乞勒纵横示告碑》(光绪五年)。
(三)民间的努力
侵垦义冢、滥挖滥掘的行为,不仅触犯官方法律,而且有悖于民间的道德习俗。伤人之坟冢,损己之阴德,是其一;破坏龙脉,妨碍县治,是其二。
为阻止上述问题的产生,民间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送官究治、禀官示禁之外,民间还自有一套预防与惩治的措施,其中以罚银、罚戏最为典型。咸丰年间,新竹地方绅民同立《员山子番子湖冢牧申约并禁碑》,约定:“窃思人生斯世,孰非无祖坟墓乎!然此牛埔内坟墓叠埋,但今之世,近来人心不古,徒知以锄草皮肥业利己,不顾他人坟墓(以下阙),不知损伤阴功之祸害耳。爰我众议演戏申禁,不许锄刬草皮。自禁以后,倘有恃强刁横违禁者,鸣众公罚银十二元。该银即存福德爷,以为香祀需费。决不轻贷!”
又如,嘉庆时,芝山地方民众曾订立合约,该处冢地树木,严禁盗砍。迨道光二十七年(1847),突有黄禄借盗砍东北古树,《芝山合约碑记》云,“时众等出首,获罚并演戏,重禁该山上下树木不许砍伤”。
可见,民间社会的常用办法是相互约定,树立示禁碑。首先,反复申明侵垦、滥挖的行为,有违伦理道德,损人不利己。其次,约定了对这类行为给予罚款、罚戏等处分。
三、结语
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以侵垦与盗墓、勒索为主要表现。然而,它们都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在祖国大陆其他地区,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年间,格尔古德任直隶巡抚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冢地,民诉于户部。可见,由土地争占造成的冢地之破坏,早已有之。不过,清代台湾义冢屡遭侵垦,则因大量未垦荒地的存在与土地所有权的模糊而愈加明显。
至于盗墓与勒索,亦见之于其他地方。道光《厦门志》载:
发冢,律有明条。开棺见尸者,分别首从,斩、绞、军、流,定罪有差。厦门前此未闻也,二十年来,此风渐炽。受害者常不自知,每至迁葬时,始觉骨骸移置,钗钏、环铛无一留存。或新死者臂上金环不可脱,断其臂取之。大抵所盗,女坟居多。盖厦地以厚葬其亲为孝,而不知适为贾祸之端。或有少妇夭亡,外家百端需索,勒令厚葬。将欲爱之,适以害之。前广东巡抚韩崶谕令民间:凡葬,富者以香木镂作钗环,贫者杂木,冠用纸胚,饰以金箔。使其中无可欲,此风当不戢自弭。揆诸古人“薄葬”之义,明器之设,颇与礼合,人子爱亲无所不至。“礼”曰:“附身附棺勿使有悔焉”而已,何忍侈其服御,致遭暴露之痛哉!愿岛中人则效之。(以上四社)。
近山大姓,恃众负嵎。遇人丧葬,或借界址不清,或借损伤坟荫,辄行阻止,得赂乃已;偶尔培土,便索酒礼,谓之“插花”。相隔一峰,讼则称破伊坟脑,伤伊丁口。山鬼从中唆弄,乡鳄大肆嚣陵。顽薄之风,至此已极,尤宜痛为惩治。
不过,这段材料对盗墓与勒索的描述,与台湾的情况有所区别。一般论及盗墓,人们总习惯性地关注利益驱使下的盗墓行为,及“厚葬”习俗的诱惑(如上文《厦门志》所载)。而清代台湾的盗墓者多是无家无业的游民,他们或迫于生计,或无所事事,目标大多仅限于盗卖山石、土砖,台湾知县周作洵叹称“牟利无多,何身命不惜”,似未企盼获取厚利。其次,游民勒索丧家的做法,也与《厦门志》所述大相径庭。前者明目张胆,后者则借助宗族势力、以“界址不清”或“损伤坟荫”等为借口,两者体现了不同的勒索主体与勒索方式。游民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既反映出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特质,又折射出其作为边疆社会的不稳定性。
自清代前期到后期,台湾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尤其引人注意。不论是社会结构从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组合到以宗族关系为主的变化,还是人口结构从以移民为主到以移民后裔为主的变化,都体现出台湾社会趋于安定、有序的局面。但我们注意到,尽管官民双方均有维护措施,清代台湾的义冢仍遭受破坏,不断涌现的示禁碑即可见一斑。实际上,土地所有权混乱的局面得不到改善,台湾义冢遭破坏的现象就很难根除。另一方面,盗墓、勒索等社会现象则反映出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行政控制力的薄弱。从史料来看,大约自嘉道起,官民双方对于这类社会问题的态度也倾向柔和。官方“息讼”的原则、“折中”的做法以及民间相互约定、加以示禁的方式,似乎都体现了台湾社会走向有序的趋势。
围绕义冢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清代台湾所独有。大致在清中叶之后,祖国大陆(如闽浙粤等省)同样受到争夺坟山、侵垦冢地、乞丐强乞等问题的困扰。不惟如此,官方与民间的解决之道,除了惩罚性的手段外,也有带着息事宁人意味的折中办法。可以说,这些足以表现清代台湾特质的社会现象,却又再次反映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相连性。
以往学界关于清代台湾社会转型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产生了“内地化”(历史学者李国祁)、“土著化”(人类学者陈其南)等解释模式。二者理论背景和实质内涵迥然相异,陈孔立先生批评性地提出“双向型”的解释模式:
(清代台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但它也不是“内地化”加“土著化”,因为直到被日本占据以前,台湾社会还没有“化”成和大陆“完全相同的社会”,也没有“化”到“土著过程已经完成”,或从大陆社会“疏离出去”,它还处在双向发展的过程之中。本来,台湾还会沿着这条双向型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和闽粤社会十分相像的土著社会,只是由于日本的占据打断了这个进程,从此,台湾社会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和大陆社会逐渐疏离了。
也就是说,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并非单向的过程,“土著化”与“内地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毫无疑问,若撇开日本侵占的影响不论,当祖国大陆移民认同居住地(台湾)、“土著化”之后,他们所建立的只能是同他们原来的母体社会(大陆)一样的社会。
本文以义冢为中心、关于清代台湾社会问题的论述,体现出清代台湾与祖国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较多的相似性。这些社会问题既能体现出清代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色彩,也印证了其作为移民社会的移植性特征。当然,由于义冢基本属于传统汉人社会的产物,本文关于义冢的讨论主要指涉汉人社会的存在形态,因而无法全面顾及整个台湾社会的面貌。
【注】文章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责编:李毅婷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Hash:0ab2ed04610b22daf86762b6f15dc7df369a420e
声明:此文由 边疆时空 分享发布,并不意味本站赞同其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kefu@qq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