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约村遗址
位于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内及北部。李家山乡统辖整个云固川,云固川河发源于金蛾山,上游分为东西两河,两河之间是一南向北高南低鱼脊形的大缓坡川地,当地俗称为鳖跌沟。东西两河由北向南流至卡约村南汇成一河,卡约村坐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处。卡约村遗址是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的,是卡约艾化的命名地。遗址面积较大,除包括整个村庄外,还延伸到村北耕地。遗址可分南、北、西三区,南区基本都压在村庄之下,大部都是农民庄院,南边缘处有少量的墓葬,北区为纯居住区遗址,西区是葬地。南区在庄院墙基下见有较厚的灰层和烧土外,很多庄院墙内都夹有杂骨和碎陶片。北区距村庄约40米,地势略高,70年代前保存完整,并于1958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秋为扩大耕地,用推土机将遗址推平,填人北部小沟内,1982年复查时尚未耕种,地面上到处是碎石、杂骨、陶片,文化层已裸露,见有灰坑、红胶泥掺细砂铺设的房屋居住面和残灶等遗迹,部分地区已见生土层。1983年已耕种小麦,遗址随之消失。西区是葬地,安特生曾在此发掘墓葬数座。由于历年取土致使西部破坏无余,东部则压在村庄之下。1983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曾在东部农民庄院内,清理残墓葬1座,系长方形立坑偏洞墓,单人二次扰乱葬式,随葬陶器3件及一些装饰品。卡约村遗址不但是卡约文化的命名地,从卡约文化分布情况看,云固川内的卡约文化遗存非常密集,是卡约人聚集地之一。
卡西诺山:二战与历史文化遗址保护
二战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各国弥足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化遗址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程度的破坏。
意大利是法西斯轴心国的骨干国之一,却也是德意日“三轴心”中第一个退出战争并反戈一击的国家,盟军和法西斯军队在意大利半岛上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死缠烂打”。众所周知,意大利是古罗马的故地,而古罗马又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这里拥有欧洲最丰富、最密集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当二战硝烟泛起,许多担心文化遗址被战争破坏的人就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有的呼吁参战各方避免战事殃及文物古迹,有的开始采取各种利索能力的手段保护身边古迹。
应该承认,在绝大多数时候,不论同盟国或轴心国都尽可能避免殃及文物古迹,以免变成历史的千古罪人。交战双方几次拉锯,罗马和佛罗伦萨两座历史名城都被双方心照不宣地定义为“不设防城市”,令这两座位于拉锯战范围内的历史名城免遭没顶之灾。德国在意大利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凯塞林空军元帅(Albert Kesselring )更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比较注意保护文物古迹,战后获得盟军将领的求情并得到轻判。

但毕竟战火无情,仍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被毁于一旦,比如著名的卡西诺山圣本笃修道院。
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 )位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弗罗西诺内省卡西诺市郊外,罗马东南约130 公里,是一座高度仅为520 米的低矮石山。公元529 年,传说中的“圣人”——天主教隐士努西亚的聖本篤(SaintBenedict of Nursia )在这里兴建隐修会所,成为著名的本笃会创始人。1220 年,圣本笃被天主教会“封圣”,受到信徒敬仰,卡西诺山就此成为“圣迹”,历代不断在山上大兴土木,修复和扩大本笃修道院,而圣本笃兄妹的墓葬也在卡西诺山上,因此当地许多人相信,战火不会波及卡西诺山,尽管战争已蔓延到意大利本土,圣本笃修道院的隐修士们仍一如既往地隐修,周围许多平民也跑到山上躲避战火。
1943 年9 月,盟军从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王国政府倒向同盟国,希特勒则派遣德军进入意大利,同时救出墨索里尼,并扶持其在北方建立傀儡政权,继续和盟军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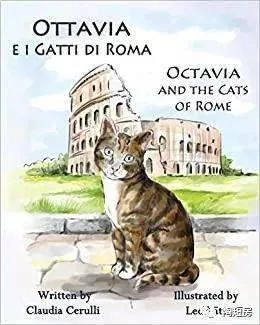

德军利用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半岛)长靴状的地形,建立一道道防线逐级抵抗,力图尽可能久地将盟军阻挡在远离德国本土的地方。1943 年底,德国第十军等部约8 万人占据卡西诺山附近的“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e ),盟军攻势受阻。
1944 年1 月17 日,坚信“德军在卡西诺山建立永久性工事”的盟军发动了卡西诺山战役,投入军队24 万,坦克1900 多辆,飞机4000 架以上,主力为美国第五军和英国第八军,参战军人包括美、英、意大利(倒戈的王国军队)、波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自由法国和印度等。
事实上,当地纳粹守军主力还是遵循了“尽量不破坏名胜古迹”的“意大利战争潜规则”,仅仅在卡西诺山的外围和山脚下布防,并没有占据修道院等真正的名胜古迹。

1 月17 日,盟军发动第一次攻势,目标是“打穿”古斯塔夫防线,占领罗马并迅速向北推进,但激战六周后,盟军付出1.6 万人的惨痛伤亡,却仅向前推进了11 公里,卡西诺山仍在纳粹军手中。
恼羞成怒的盟军将领相信,纳粹之所以如此难打,是因为其炮击十分准确,而之所以如此,“一定是纳粹在圣本笃修道院建立了炮兵观测所”,而当时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著名新闻记者苏兹伯格(CL Sulzberger )极力游说盟军将领,使之相信这一说法,地中海盟军空军总司令艾克中将(Ira C. Eaker )亲自飞临卡西诺山上空侦查,据说在修道院里发现无线电天线和晾晒的德军衣物,回来后就以此为依据,力主炸毁圣本笃修道院,以免被德军利用。绝大多数盟军将领支持这一说法,仅有少数人认为“证据不足,且即便如此也无关紧要,没必要为此破坏如此珍贵的文物古迹”,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英属印度第四师师长图克少将Francis Tuker 成为令圣本笃修道院陷入灭顶之灾的“杀手”:他不仅坚信“修道院是德军炮兵观测站”,而且特意跑到那不勒斯,去买了一本详细介绍修道院构造、出版于1879 年的旧书,并据此认定,修道院高46 米、厚3 米的石墙坚不可摧,必须用4000 磅重的超级炸弹才能奏效。
这个建议令直接负责进攻卡西诺山的美国第五军军长克拉克中将Mark W.Clark 吓了一跳,他迟迟不肯下令,但图克少将越过克拉克,直接向盟军意大利战区总司令、英国人亚历山大元帅The Earl Alexander of Tunis 汇报,后者亲自游说,最后克拉克万般无奈,回应“除非你直接这么命令我,我才干”——然则他很快收到了这个命令。
1944 年2 月15 日上午,142 架B-17 、47 架B-25 和40 架B-26 轰炸机对圣本笃修道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轰炸,总计投下1150 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在这期间盟军炮兵还对修道院发起猛烈炮击,整个修道院被炸为一片废墟,引起山下支持轰炸的盟军将领阵阵欢呼,而反对轰炸的克拉克等人则索性躲到了后方。
轰炸引起方方面面的愤怒:美国高级外交官提兹曼几天后拜访梵蒂冈,教廷枢机主教秘书马里奥Luigi Maglione 对他怒吼“轰炸圣本笃修道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行径”。
事实也的确如此。
盟军侦察机所看到的“德军痕迹”,只是部分受到救治的德国伤员所留下的,这并不违反任何战争法则。在圣本笃修道院被彻底炸毁前,修道院里只有意大利人常驻,从未被据为炮兵观察哨。轰炸在修道院内造成230 多人死亡,但这些人或是拒绝撤离的修道士,或是相信“打仗不会波及古迹”前来避难的意大利平民——当然,也的确有几十名纳粹官兵被炸死炸伤,但他们都是被不小心投歪了的炸弹炸死在远离修道院的阵地上的(因为天气不好,当天有近90% 的炸弹投歪了)。
2 月17 日,修道院院长、79 岁的迪马亚雷(GregorioDiamare )带领幸存者逃离卡西诺山,第二天他们被盟军发现,盟军此刻才知道自己犯下了何等愚蠢的错误:近300 名避难平民中仅约40 人得以逃脱,而修道士则仅幸存6 人。
既然修道院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纳粹方面觉得“不再有义务遵循潜规则”,伞兵1 师随即占领了修道院废墟,将之作为防线的一部分——此时这里反倒真的成了要塞和炮兵观测所,并给盟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此后盟军对卡西诺山发动持续猛攻,但均不奏效,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被炸成瓦砾的修道院反倒更难攻打——不规则的瓦砾堆让善于“打乱战”的德国伞兵如鱼得水,习惯于正规战的盟军却怎么打怎么别扭,而且再怎样空袭也都适得其反。
直到5 月18 日,鉴于两翼防线都被突破,纳粹军队才主动放弃了早已面目全非的卡西诺山。
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出资修复了圣本笃修道院,时任教皇保罗六世PopePaul VI 则协助募集了大量修复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并非什么“秋毫无犯”:他们用大卡车在战前把1400 册最珍贵的手抄本从圣本笃教堂窃取,并于1943 年12 月送给帝国元帅戈林Hermann Göring, 当作寿礼——但此举和盟军的轰炸一样适得其反,战后被当作战犯判处死刑、并在执行前自杀的戈林并未能消受这份厚礼,这些珍贵的手抄本却因为帝国元帅的贪婪,鬼使神差地躲过了1944 年2 月15 日从天而降的大劫难。
漯河发现一处距今约7000年的文化遗址!
3月6日,区文物部门接到群众反映:在李集镇后倪村,有一村民栽种梨树过程中,挖出一些陶片、石化鹿角、人骨、红烧土层、大量蚌壳等器物。接到报告后,区文物部门立即派专人前往实地查看并向市文物局、市考古所汇报情况。

经市文物部门和市考古所专家实地走访调查和现场勘察,通过对出土器物、周边土层进行分析研判,从其文化特征综合分析,初步判定为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距今约7000至5000年),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它的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对研究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的过渡及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性质等诸多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目前,区文物部门将对遗址的周围情况、面积做进一步的调查,并做好保护工作。
来源:精彩郾城
山西发掘距今约4000年龙山文化聚落遗址
经过四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晋城下町遗址揭露出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人类聚落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






下町遗址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瓮罐葬

仰韶时期陶窑

龙山时期陶窑
下町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下町村西南处,在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今年6月,为配合晋阳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晋城市、泽州县文物部门,对该建设工程涉及的遗址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该发掘项目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武俊华介绍,长期以来,山西考古的重点一直在晋南地区。晋东南地区特别是晋城地区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少。此次涉建区域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是晋城市历史上第二次发掘史前时期遗址,为研究晋城地区史前文明进程提供了客观翔实的实物依据,成功构建了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填补了晋城地区龙山时期遗址考古工作的空白。
此次下町遗址发掘面积为2000平方米,分东、西两区。共清理出灰坑150个、陶窑2座、竖穴土坑墓8座、瓮罐葬1座、房址1座,时代涵盖仰韶、龙山、二里头、东周等多个时期,其中以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器型有盆、罐、瓮、碗、钵、豆、鬲、甗、斝、鼎、尖底瓶、纺轮等,纹饰有绳纹、弦纹、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素面等。石器有石铲、石刀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骨针等。其中可复原的完整陶器标本约50件,另外还有130余件小件器物标本,总体陶器标本数量接近1000件。在东侧一探方中,还发掘出一个大口尖底陶罐,并于罐中发现孩童遗骨。武俊华说,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电子版
图片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1日09版、 太原日报等媒体










